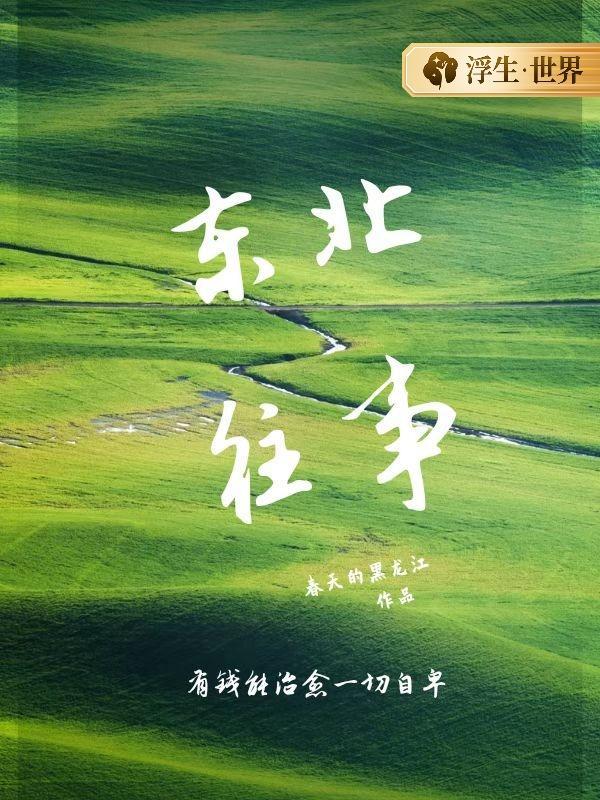小说铺>问九卿 > 第186章 黯牢(第1页)
第186章 黯牢(第1页)
李肇踩着积水回到幽篁居时,来福正捧着药碗,看着空荡荡的屋子,急得团团转。
冷不防见到主子推门而入,惊得他手中药汤荡了出去。
“殿下!”来福慌忙放下药碗,跪地请安,目光落在李肇浸血的外袍上。
“您肩膀又渗血了?”
“无碍。”李肇扯开浸血的外袍,露出胳膊上蜿蜒的血痕。
来福这才看清,那不是结痂的旧伤出血,而是新的创口,血珠正顺着臂弯往下淌,滴在青砖上……
“我的爷,怎么又受伤了……”来福慌乱不已,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,说着便要去找张怀诚来问诊,被李肇冷声制止。
“休得声张!”
来福喉间一哽,眼睁睁看着自家殿下扯过素白汗巾按住伤口,心下就明白了几分——定与那平安夫人有关。
好端端的一个人,跟着她出去,受了伤回来。
这女子……有毒吧?
看着殿下单薄的身影,来福躬着身子,忍不住嘟囔,“自从殿下结识了平安夫人,身上的伤病就没有断过……不是吃药就是疗伤……”
“多嘴!”李肇冷眼,眉峰在痛楚中微微蹙紧,“还不把药箱找来?”
“是!”来福忙不迭取来药箱,跪在李肇脚边,双手微微颤抖着,小心翼翼解开他的中衣。
看到那几乎贯穿臂膀的箭伤时,来福心疼得跟什么似的,眼眶一红,泪珠子差点滚下来。
“爷啊,疼得厉害吗?”
李肇闭目隐忍,任那钻心剧痛漫过全身。
“若敢泄露一个字,孤要你的脑袋。”
不是他不信任张怀诚,而是李桓心思太过缜密,连情丝蛊那般隐秘的消息都能探听出来,不得不防。
少一个人知道,便少一分风险。
“小的明白。”来福捧着金创药瓶,犹豫片刻,还是壮着胆子提议,“要不……把平安夫人叫来,为殿下疗伤也好……”
李肇睁眼,目光扫过那带血的衣衫,眼底不经意间闪过一丝冷意。
“不必。”他接过药瓶,将金创药细密地洒落在伤口,又不慌不忙地缠上一层一层的纱布……
“她此刻怕是焦头烂额,自顾不暇——孤那皇兄,向来不是好相与的。”
话音未落,窗外夜鸦啼叫,惊起一片寒枝。
雨声淅淅沥沥,混着金创药的苦味在殿内蔓延。
李肇摆了摆手,示意来福退下,半倚在软榻上,对着暗处轻声。
“进来。”
夜枭瘦削的身影从阴影里的暗门出来,单膝跪地。
“殿下请过目。”
他手上捧着一份密函。
李肇面色如常地展开密信,赫然看到西兹的图腾。
“西兹王杀父继位,屠戮王室,清洗旧臣,意欲斩草除根。”
一行字在烛光下触目惊心。
李肇瞥他一眼,未束的长发垂落肩头,烛光在他苍白的脸上,投下深深阴影。
“近来出入上京的西兹商队,以及公主府的动静,事无巨细,皆要呈来。”
夜枭拱手沉声:“属下领命!”
婉昭仪在行宫暴毙的噩耗,当日便传到了紫宸殿。
崇昭帝龙颜大怒,连夜召见了礼部尚书,命其为昭仪娘娘治丧。
第二日早朝,皇帝又当众叹息,满是哀伤地道:
“昭仪生性温良恭俭,淑德可风,朕竟令明珠蒙尘十余载,实在悔恨不已啊!”
明面上,皇帝深情追思,下旨追封婉昭仪为懿妃,命太常寺以皇妃的仪制举哀,恩宠有加。
暗地里,他再派大内侍卫数十人,以保护文嘉公主,寻找失踪的妞妞为名,查探文嘉是否与西兹有牵连……
朝堂之上风云突变。
数日后,御史周仲平率先发难,矛头直指端王失职。